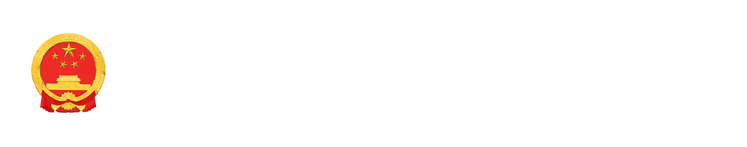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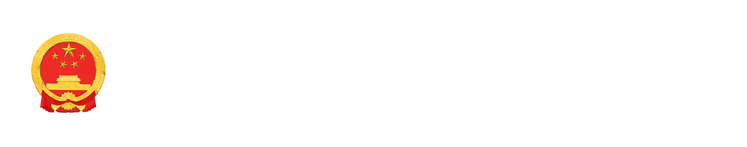
以借为名拿走他人手机的行为如何定性——从占有处分权区分财产罪构成
合肥铁检院 丁永忠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17日中午,被告人张某在合肥火车站第二候车室内,以钥匙忘了给他表哥了为借口,向女旅客李某借用一部价值4810元的苹果手机打电话,尔后将自己的双肩包放在座位让李某帮忙看着,张某在借到手机后边打电话边向往候车室外走,李某发现情况不对,追出候车室却找不到张某。
同年11月10日傍晚,被告人张某在合肥南火车站北售票厅内,以自己的手机停机了,想向朋友打个电话借点钱为由,向一女大学生刘某借用了一部价值1867元的OPOP牌手机。尔后,装作打电话走出售票大厅,刘某紧跟张某走出大厅,但张某仍快步摆脱了刘某并携机逃走。
同年11月26日中午,被告人张某在合肥火车站肯德基餐厅内,故伎重演,向女旅客钱某借用一部价值2230元的OPOP牌手机,之后装作打电话,以室内信号不好为由,走出门外携机逃走。
[主要争议问题]
该案对被告人张某的定性上,一般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张某对手机只是暂时拥有手机的使用权,且是在被害人的面前使用,没有对手机的占有处分权,只是在被害人不备的情况下将手机携带逃走,符合秘密窃取财物的特征,故其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张某以借手机打电话为由,骗取三名被害人信任,使三名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将手机自愿交付给张某占有,张某却携机逃跑,故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理由是被害人将手机借给张某使用,是一种自愿委托对方管理财物的行为,张某将自己保管的财产非法占有,符合侵占罪的特征。
第四种意见: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理由是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趁人不备公然夺取较大财物的行为。
[观点评析]
笔者认为:张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抢夺罪,皆为取得财产罪。取得罪是财产罪的中心。取得罪是指不法取得财产的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等。取得罪又可进一步分为夺取罪和交付罪,前者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如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后者是被害人基于意思瑕疵而同意交付财产的犯罪,如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下面,笔者试从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抢夺罪的构成要件,从财产的占有权和处分权方面,对这四种财产罪进行比较,以便准确为本案张某的行为进行定性。
1、盗窃罪
该罪在我国刑法上是这样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盗窃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同时通说认为,只要行为人自认为被害人没有发觉而取得的,就是秘密窃取。但理论界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张明楷教授就认为:盗窃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如果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则必然存在处罚上的空隙,造成不公正现象。国外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均不要求秘密窃取,事实上完全存在公开盗窃的情况。该观点指出通说理论所存在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通说混淆了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区别。既然是“自认为”,就意味着“秘密”是主观认识内容,而不是客观构成要件内容。其二,根据通说,同样在客观上都是公开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当行为人自认为被害人没有发觉时成立盗窃罪,认识到被害人发觉时就成立抢夺罪。此观点是错误的。其三,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行为人在以平和方式取得他人财物时,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为他人发觉。根据通说,便无法确定该行为的性质。通说也可能认为,此时应根据客观上是否具有秘密性区分盗窃与抢夺。但这又与通说的定义相矛盾。其四,仅凭行为人“自认为”秘密或公开决定犯罪性质,也容易造成定罪的困难。其五,故意的内容与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是一致的,构成要件规制故意的内容。一方面,凡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就必然属于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另一方面,凡是不属于客观构成要素的事实,就不可能成为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其六,公开盗窃的情形大量存在。例如,进入他人住宅后,明知卧床不起或者胆小的占有者盯着自己,但依然搬走他人的电视机。再如,明知停车场管理者看守着他人的自行车,仍然偷走自行车。既然如此,刑法理论就必须面对现实,承认公开窃取行为构成盗窃罪。张明楷教授指出,窃取的手段与方法没有限制,即便使用了欺骗方法,但如果该欺骗行为并不具有使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性质,仍然成立盗窃罪。例如,行为人伪装成顾客,到商店试穿高档西服,然后逃走的,也成立盗窃罪。[*参见张明楷的《刑法学》,2011年7月第四版,第877-878页]
从本案张某作案方式来看,其非法占有手机,既有趁被害人不备的悄悄溜走行为,也有在被害人面前公开逃走的行为。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以上两种行为皆是窃取财产的行为,无论是秘密窃取,还是公开窃取,皆应定性为盗窃罪。
2、诈骗罪
该罪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在诈骗罪的构成中,被害人因受骗而基于处分财物的故意支配下,实施了一种处分财物的行为,即:把自己的财物给他人仅仅是因为受被告人的蒙骗实施的,这种处分行为是有重大瑕疵的,在民法上是无效的。但在刑事上看来,行为主观上有处分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处分了自己的财物,是典型的交付,是自愿交付的,且是基于处分的意思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的处分。处分的意思,意味着把自己的财物的占有转移给他人,是一种转移占有的犯罪。因此,能否认定为诈骗,就要看占有关系是否转移。在某些情况下,虽然财物移交给他人,但占有关系并未转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诈骗,但是究其本质不能认定为诈骗罪。
本案中,张某虽然实施了借用手机的欺骗行为,但被害人并不是将自己的手机交由张某占有处分,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借用,且是在被害人监视之下的借用;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将手机借给被告人,并不意味着丧失了对手机的控制,手机尚在被害人控制之下,而张某实质上对手机并无占有权;张某只是暂时持有手机,其以借为名,是为其窃取手机创造条件,而其拿到手机后的逃离行为导致了被害人丧失对手机的占有,这种行为的本质是违背被害人的意愿。因此,该案不构成诈骗罪。
3、侵占罪
该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较大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的行为。侵占罪与盗窃罪在客观方面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被害人的主观意愿及行为人客观上获得财物的方式。侵占的被害人有自愿委托对方管理财物的行为,而盗窃罪的行为人获取财物的方式为窃取。本案被害人仅有暂时出借手机让张某打个电话的意思表示,并无委托张某对手机过长时间的管理行为,不能将被害人出借手机的短暂期间扩大理解为双方产生保管关系。该案由于被害人只是短暂的借给张某打电话之用,主观上不存在委托张某保管手机,手机的占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张某没有对手机的自由处分权,因此本案也不属于侵占罪。
4、抢夺罪
该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趁人不备公然夺取较大财物的行为。在本案中,张某并不是公然从被害人手中夺取手机,所以其不符合抢夺罪的犯罪构成。
综上所述,本案张某以借用手机打电话为名,尔后伺机逃离现场将手机非法占有的行为,是一种窃取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特征,所以张某构成盗窃罪。